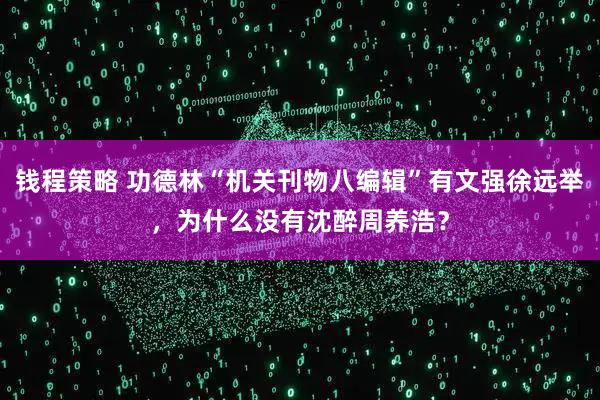
我们看《特赦1959》就会发现,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,最有技能的是叶立三,最搞笑的是蔡守元钱程策略,最难改造的是刘安国,但是您翻遍七批特赦名单,都找不到这三个人的名字,倒是那个跟妻子跳舞的陈瑞章,在第七批特赦名单中找到了一个跟他名字相似的人,那就是第十二兵团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。
叶立三和蔡守元、刘安国无疑是在电视剧中用了化名,我们根据相关史料分析,张淦就是桂系大将、第三兵团司令、有“罗盘将军”之称的张淦,刘安国的历史原型,就是1926年入党、参加过南昌起义、在军统时期就晋升中将,被俘时任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、代参谋长的文强。

文强1975年特赦之后担任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、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、文史军事组副组长,不但组织、审核了大量特赦人员的回忆文章,自己也写了不少,笔者买到了他的《文强口述自传》《戴笠其人》《新生之路》,尤其是那本《新生之路》更有意思,那才是以第一视角回顾自己和“同学”们的学习改造生活,比沈醉的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在时间地点和人物方面更加详实准确——沈醉更注重写“趣事”,而文强则记录了很多人的心路历程。
王英光是这样介绍刘安国的:“他是一九二六年入的党,参加过南昌起义,三十年代初的时候,在我党还担任过相当的职务,我党党史上的事,他知道的比我们清楚。”
这就跟《文强口述自传》对上号了:“李鸣珂牺牲(文强用的是另一个字)了,省委要我接替他的这个位置,当了省委常委。后来,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,我领导二十三个县,是很大的一块根据地。1931年,我被捕了……”
文强被捕获救后,因为不愿意接受严格审查而去上海找他的入党介绍人,寻人不遇后被戴笠招揽,并在程潜张治中等人运作下取消了通缉令,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电视剧里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叛徒——他既没有出卖组织,也没有出卖同志,是在失联状态下转换了阵营。

李明珂和文强都是黄埔四期生,黄埔四期出了很多名将,当年在东北战场上,就有至少四位黄埔四期生的级别很高,双方各有两个,老蒋那头的是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、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文强和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俦(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)。
文强多次在回忆录中提到过他另两位黄埔四期同学钱程策略,因为有些话不便复述,咱们还是放下不提,接下来只聊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的表现——他跟徐远举一样,都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顽固,要不然也不会成为功德林“最有话语权”的八位“同学”之一了。
这个“话语权”之所以要加引号,是因为这八个人都是“功德林学习委员会机关刊物”《新生园地》的主编和编辑——如果把《新生园地》比作一张报纸,那么文强就是“文艺副刊部主任”,尽管这个主任可能手下连一个编辑都没有。
功德林学员当然不可能办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,文强在《新生之路》中说的“机关刊物”实际就是我们在上学时都办过的墙报——现在很多教室的后面墙上,依然还有墙报。

谁能在功德林的《新生园地》负责一个专栏,那可是要经过千挑万选的,而且“岗位竞争”也一定很激烈,文强最后记录的人员名单是这样的:主编,陈远湘;美术编辑,郭一予;理论专栏由宋希濂、廖耀湘、陈林达负责,挑战应战专栏由李帆群负责,批评表扬专栏由徐远举负责,文艺专栏由文强负责。
李帆群在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中“表现不佳”,沈醉也是一个“有艺术细胞的文化人”,而且学习改造也相当激励,他连一个专栏也没捞着,可能有些失落,就对这么重要的一个“刊物”的编审人员名单只字不提,但也说了这个阵地很重要:“当时在管理所‘新生园地’壁报上贴东西,可以说是相当民主的。谁想写什么,都可以贴出去,错的东西,自然会有人来写东西纠正,打笔墨官司的事是常有的……我诗兴大发,口占一绝,这一类诗词,是不能登庄严肃穆的墙报‘新生园地’的,我只能写在日记本上。”
沈醉写诗要想“发表”,自然是要过文强那一关的,虽然文强表示“文责自负”自己绝不“毙稿”,但功德林有那么多将军级“才子”,显然不可能所有的“诗作”都能“发表”上去,笔者在上学的时候,也没少“处理”类似的“纠纷”。

文强是一位“特殊人物”,功德林的许多管理规定都是他参与制定的,这件事他在《口述自传》中有详细描述:“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规定贴出来,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。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,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,后来所长长换了人,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,叫姚伦,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,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,是很好的朋友了。我每天在所里忙得很,当学习组长,又管墙报,管文艺,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,我又在这里负责,过年过节,还写些纪念的文章。”
邱行湘(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师长,1959年第一批特赦)的外甥黄济人在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中也证实了此事:“功德林各条胡同的房间里,都贴上了一张八开大小的纸张,上面油印着十几行文字。文强仰面之前,不觉暗暗得意,待他过目之后,不觉暗暗惊奇。”
文强和姚伦参与拍摄的那部电影就是《决战之后》,想必很多读者都看过,笔者看了之后也有点想笑:文强起码是个不挂名的顾问,怎么不找个英俊一点的演自己?

文强并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“倔强”,但他知错不认错却是真的,真正令人奇怪的,就是脾气暴躁、绰号“猛子”的原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、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,怎么能跟宋希濂、文强等人“平起平坐”,而且负责的是那么重要的“批评表扬专栏”?
文强在《新生之路》中给出了答案:“批评表扬专栏比较集中于生活问题,徐远举性情暴躁、作风强悍,这些年来几次重病,都是政府派医生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,他感恩忏悔,认罪态度很好,学习劳动也积极,但性情和作风依然故我。只要发现不利于改造的事情,如扯皮打架、分菜不匀、清洁卫生不负责、浪费公物等违反新生公约的自私自利现象,从不放过,他每每文不起稿地、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,加以生得豹头环眼,不顾人情世故,令人望而生畏,我曾写过一首小诗借以开导,他却紧握锋利的笔对我说‘笑骂由人笑骂,批评我自为之’。”
看起来徐远举这个罪行累累的大特务,经过多年改造,确实已经有些“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”的意思了,但他的暴脾气一直没有改变,所以没能等到1975年的全部特赦。

发生在文强和徐远举这两个“犟脾气”身上的巨大变化,让我们不能不感叹改造战犯的成功,同时我们也不禁想起了文强和沈醉在军统的“同行”沈醉和周养浩:沈醉1960年特赦后又“进去了”,周养浩1975年特赦后要去台湾吃了闭门羹也没回来,这两个人真的完全改造好了吗?
沈醉的五本回忆录笔者都买全了,细看之下才发现其中有些许自相矛盾之处,跟其他特赦人员的回忆文章也有些出入,于是就有了留给读者诸君最后的问题:文强和徐远举都当了《新生园地》的专栏负责人,掌握着很大的话语权,沈醉为什么一个专栏都没捞着?说到墙报专栏,上过学的读者,一定能回想起很多有趣的事情吧?您有没有用雪糕和糖块从“编辑”手里换取自己“稿子上墙”的机会?或者说您当“编辑”的时候,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话语权很大?
红腾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